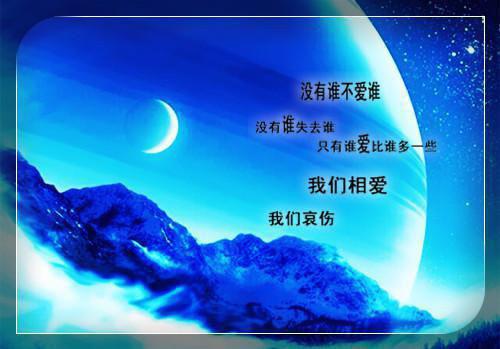文字能行多远
|
时常会有一些人会在看过个人的小说之后追问:这是真实的吗?但个人永远都只有一个回答:不是真的。
一个朋友发短信过来说,她读我和另外一个写手朋友的文章有着不同的感觉,那个朋友的文章可以让她落泪,而我的却很平淡。但事后在生活中做许多事时,总会想到文字中对应的情节或哲理,于是不知不觉受其影响。还是很开心可以得到别人这样的评价。其实知道,自己的文字并不算华丽,也不能算绚丽,更多的都只是一种平淡,唯一可以让自己超脱开的,便是一点思想。也许是天生就是显得比他人老吧,总是要想得比他人更多些。比如小时候就开始想一个时间、生死的问题。那时总是不肯相信有一天自己要老去,要死去,总觉得这一个世界是伴随着我而生的,所以世界不消亡,那么我也不该有死亡。但却又知道,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看着自己身边的亲人,岁月在他们的身上重叠着,又交错着,于是他们也就各自呈现不同的生命姿态,知道自己也避免不了。但那时,真的可以单纯地去相信,这个世界没有历史,没有秦始皇,没有李世民,他们只是一个传说,如同月亮中的嫦娥一样,只是子虚乌有。只是如今,无论如何地不愿意,却也被时间一点一点地拉扯着长大,看到了许多想看、不想看、该看、不该看的画面,经历了许多渴望、厌恶、无奈、逃避的事件,于是心一点一点地苍老着,再一点一点地折射出这个世界逐渐黯淡的光芒。投入到文字中,便多少沾染了一点沉重,岁月积累起来的垢痕。 只是真的不知道文字可以牵引自己的生活有多远。努力地让文字变得纯净,不是指文字的内容,文字的风格,而是指写作的心态,简单一点,不必去想他人的评价,不去想能否换来稻粱,换来功名,一切只是顺应着个人的心情,顺由着个人的兴趣,滑溜开去,能够走多远就多远。无意成名,亦无意换来黄金屋,颜如玉,只是希望可以借此与时间对抗些,还有的,希望文字能够引领着自己找到一些相通的灵魂,彼此在观望对方的时候,浮现出自己灵魂的模样。然后,彼此能够牵手是最好,渐行渐远也不必多去感伤。就如同泰戈尔的那一句: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,而我已飞过。飞翔不是为了在天空中留下标记,而只是一种生命的姿态,一种自由的放纵。共2页,当前第1页12 对于文字与生活的关系,其实一直是很喜欢以前的那一个标题:文字的围城。以文字来困住生活,又以生活来推行着文字。于是生命的体验,可以更加地纤毫毕现,而文字的空间,又会拓展开生活的视角。只是尚且无法做到以生命来写作。那是余光中所谓的写作三境界的最高境界了——以知识写作,以才华写作,以生命写作。但始终觉得,以生命来写作的人,往往要将自己逼到残忍的角落里去,要去对自己残酷,在那鲜血淋漓中体验生命的各种不同滋味,换取文字的鲜灵,比如顾城,那一个以斧杀妻又自杀的人;比如郁达夫,那一个为推动着文字的反省而时刻剖析自己的人,最终让自己陷入了病态的心理。现实生活中见过的人不少,有的是以摧残自己的生命来寻求文字的灵感,有的是以自断前程的追求来换取对文字的虔诚。但知道自己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。或许我本来就是以文字来换求一种灵魂上的安宁,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激烈反抗,对个性自我的热烈召唤。 一直是有点不太喜欢对文字赋予过多功利性欲望的人,而对于那些因为文字而沾沾自喜的人,也不是很喜欢。但却不反对因为文字而滋生的傲气。或许是因为自己无法免俗而又无法自我鄙视所给自己留下的理由吧。但文字若无傲气,往往也就是没有了个性,没有了个性,往往也就是没有了性灵。而市侩,则更是会直接地抹杀了性灵。另外地,一直也都很恶心那一种以文字来为自己的生活或个性来粉饰的人。比如余秋雨,比如张晓风。对于前者,是因为后来看了他的一系列炒作,比如吹捧深圳,比如与余杰的对质,还有的声嘶力竭地批判小人,自己仿佛永远只是一个无辜者的姿态;对于后者,却只是源于大学时代的一次她的讲座,她的盛气凌人,她的极端摆架子,都让自己对她所有文字积累起的美感消失殆尽。于是再看她的文字,看她描述的生活世界,总觉得好虚假,总是忘不了那一个画着浓浓的妆,对学校中文系老教授出言不逊的恶俗女人。于是喜欢余光中,喜欢简贞,喜欢周国平,喜欢张贤亮,他们要么是谦逊的学者,要么是那一种不惮暴露自己灵魂阴暗面的人。还是宁愿喜欢真小人,也不愿看到伪君子了。可是文学上的伪君子实在太多,比如培根,比如卢梭,比如罗曼•罗兰。包括如今在各大文学网站里遇上的许多写手,真正称得上真诚的,并不能多。 看着笔下的文字,总是罗嗦而又沉重。哎,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改变风格,也改变对生活的态度。只是不知,那时候是否还写得出文字? |